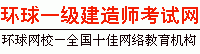刑法视域中的水资源保护
一、我国法律对水资源保护的范围
我国《水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水资源也仅限于这一范围,即陆地水资源,它包括—切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水库、池塘、冰川、积雪等所含的水,地下水一般指位于地壳上部岩石中的浅层地下水。
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随着社会生产的迅速膨胀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日俱增,而水资源的低开发利用率和水质的污染又使这一矛盾不断加剧。由于多年来对水资源的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理,我国已出现诸如水质下降、地下水超采、城市地面下沉、城巾生活用水危机、大河断流、河湖干涸萎缩等一系列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制约社会发展的问题。因此,对水资源的保护刻不容缓,刑法的介入也是必然的选择。刑法虽有介入水资源保护的必要,但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是一个首先值得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当今对水资源的破坏活动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副产品,刑法的过多介入可能阻滞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刑罚是最严厉的国家强制方法,刑罚使用不当潜藏着侵犯人权的巨大危险。因此,我们在确定刑法对水资源保护的范围,即将哪些破坏水资源的行为犯罪化时仍然要 “严格区别犯罪行为与道德违反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行政不法行为,坚持刑罚干预的谦抑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最后手段性原则,严格控制刑罚触须延伸的范围”。我国对水资源的保护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事、行政法规,如《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它们在水资源的保护中发挥着广泛、积极的作用,只有当这些法律不足以制止破坏水资源的行为时,刑法才能介入,具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水资源免受污染
水作为一种流动的资源,一旦被污染,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叫能引起人畜中毒事件,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另‘方面,水资源的污染会使生态环境恶化,引起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例如引起动植物大量死亡以至绝迹、土地沙化、盐碱化等。并且,水资源被污染后的净化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根本不能再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见,污染水资源的行为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因此,现代各国刑法无不将污染水资源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用刑罚手段保护水资源的清洁。我国水污染形势非常严重。水被污染后重新净化需要较大的投入,从而提高生产成本,不少生产单位往往将污水直接排出,进入水循环系统。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这些行为仅依靠行政经济手段很难全面禁止,达不到遏制的日的。故而刑法的保护显得十分必要。
2.保护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根据《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水资源的有限性和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山国家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为此,《水法》第11条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按流域或者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但在实际生活巾,由于对局部利益的追求,有些单位和个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不顾全局,进行破坏性或过度的开发,这种情况在缺水地区尤其严重。对水资源的破坏性或过度开发易造成两种后果,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破坏水的自然循环,引发大河断流、湖泊干涸、地面下沉等环境问题。这些灾害发生后补救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易引发社会矛盾,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例如在我国缺水地区,特别是在农村,在用水高峰期经常有争夺水源而引发群众械斗的事件出现。因此,为了防患未然,那些破坏性或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行为,应纳入刑法视野。
3.保护有关的水工程、设施的安全
为了充分、合理、安全的利用水资源,国家不惜投入巨资兴建了大量的水工程及有关设施,如堤防、护岸、大坝、防汛设施、水文监测设施、导航、助航设施等。这些设施是国家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管理、统一规划和防汛抗洪必不町少的设备。对水工程及相关设施的破坏不仅毁坏了国家财物,侵犯了国家财产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权,其社会危害性不可低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洪涝灾害频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厂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如1998年夏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在此情况下,运用刑法手段保护水工程设施的安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现状
关于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我国79《刑法》中并无相应的条款。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对水资源的刑法保护采用的是附属刑法的形式,这些附属刑法规范主要存在于两部法律中。一是《水污染防治法》第57条规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典(79《刑法》)第115条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水法》第46、47、49、50条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这些条款都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定刑,仅仅规定“依照”“比照”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而可操作性差,司法实践中适用很少,没有充分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97《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对部分原来的附属刑法规范进行了归纳、整理、完善,使之成为新刑法的一部分,但仍有一部分没有被采纳进新刑法。对此我国法学界反应冷漠,很少有人讨论究竟哪些规范被纳入了新刑法,与新刑法的哪条规范相对应,哪些规范没被采纳进刑法典,其效力究竟如何,能否继续适用。不少1997年以后出版的资源环境法方面的教材、专著,其中绝大部分在论及水资源的刑事责任时简单地把《水法》的46、47、49、50条罗列进去,而没有与新刑法进行对照。在此结合97新刑法典对原有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附属刑法规范作一简要分析。
《水污染防治法》第57条规定的水污染事故罪已并人新《刑法》第383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新《刑法》第383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于此类行为应直接适用新《刑法》第383条,原有附属刑法条款已失去效力,不再适用。
《水法》第4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擅自修建水工程或整治河道、航道的;(二)违反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擅自向下游增大排泄洪涝流量或者阻碍上游洪涝下泄的。这条附属刑法规范在97《刑法》中也有相对应的条款。其中第一项规定的擅自修建水工程或整治河道、航道的行为可归人新《刑法》第 117条的破坏交通设施罪。因为擅自修建水工程或整治河道、航道,是对原有航道的“破坏”,只要足以使船只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应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第二项规定的擅自向下游增大排泄洪涝流量或者阻碍上游洪涝下泄的行为可归人新《刑法》第115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发生洪涝灾害时,国家的统一调度对抗洪的胜利起决定性的作用,若有关单位和个人擅自向下游增大排泄洪涝流量或阻碍上游洪涝下泄,无疑将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应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可见,《水法》第46条实际上规定的是与水资源有关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而不是危害环境的犯罪,因为这些行为直接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罪所造成的人的死伤和财产损失往往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后果,而在危害环境罪中,人的死伤和财产损失仅是犯罪行为的间接后果,犯罪行为首先危害的是环境,通过环境的媒介才危害到人的安全和造成财产损失”。
《水法》第47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毁坏防汛设施、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和导航、助航设施的;(二)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危害水工程安全的活动的。本条规定在新《刑法》中无明显的体现。其中第一项中的毁坏导航、助航设施的行为可归人破坏交通设施罪。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毁坏防汛设施、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行为勉强可归人毁坏财物罪,但这些设施不仅仅是体现国家的财产权,还体现了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使用权,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了公共安全,若把这些行为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十分牵强的,并且与同项规定中的毁坏导航、助航设施的行为罪刑不均衡。至于第二项中的危害水工程安全活动的行为在新《刑法》中更是被遗忘的角落。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这些行为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无法对之定罪量刑。
《水法》第49条规定的盗窃或者抢夺防汛物资、水工程器材,贪污或者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移民安置款物的行为分别符合新《刑法》中有关盗窃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第50条规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只是新《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具体表现形式。
三、现行刑法对水资源保护立法缺陷及完善
通过上述刑法对水资源保护范围的探讨和具体刑法条款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现行刑法在水资源的保护方面介入不够,有待完善。
1.保护的范围不全面
首先,《刑法》并没有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保护,看来立法者还没有摆脱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我国的水资源十分有限,加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长期以来工农业用水的严重浪费,使得我国在用水上供求矛盾突出。为了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总体控制,我国《水法》规定了取水许可制度。那么对那些没有取得取水许可证而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大量取水的,或者虽然取得许可证却采取破坏性手段取水的,如过度抽取地下水的行为该如何对待呢?当然可以先用行政法调整,但刑法应提供一个最后的保障,将这些行为犯罪化(当然还有一个量的限制),从而增大行为成本,达到遏制的目的。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刑法》对其他资源,如野生动植物资源、渔业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提供了保护,分别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晶罪、非法狩猎罪、非法采矿罪、滥伐林木罪等。水资源与上述各种自然资源一样具有有用性和有限性,同时具有生态价值,理应受到同样的保护。建议在刑法中比照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规定,增设“非法取水罪”和“破坏性取水罪”。
其次,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行为在《刑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这些设施不仅对水资源的安全合理开发与利用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公共安全,因而对这些设施不提供刑法保护也是不合理的。我国刑法中有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建议增设“破坏水工程、水文设施罪”。
2.刑事法网不够严密,保护的力度有待加强
我国刑法中的环境资源方面的犯罪大都以“危害结果”为必备要件,从而将很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出刑法的范围,这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与其他犯罪不同,其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表面联系并不太紧密,时空的跨度也较人,但损害结果一旦发生,则会对公共安全和环境质量产生巨大的非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损失。如果坐等实际危害结果出现再用刑法,则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并无人大的意义,因为刑法手段并不能阻止危害结果的延续。因此许多国家的立法规定,只要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就可以构成犯罪。
如《瑞典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故意或过失地违反政府本法第10条发布的指令或者违反依本法第43条第 1款发布的禁止令,除非情节轻微,可判处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日本《大气污染控制法》也规定:违反根据本法第9条之一、第9条之二或第14条第1款或第3款规定而发布的命令者,处1年以下惩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我国刑法在惩罚危害环境资源方面的犯罪时,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不能仅 惩罚结果犯,还应惩罚行为犯、危险犯,从而加强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强化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
以上从立法的角度对水资源的刑法保护及其完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对水资源的保护不是制定几条法律规范就能实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要使水资源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污染、破坏水资源的犯罪及时立案侦查和起诉,需要环境与资源监督管理部门对构成破坏水资源犯罪的案件及时地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避免以罚代刑。总之,保护水资源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用好刑法这一有力的工具,使我们的家园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考试考试网一级建造师编辑整理)
上一篇:水市场的特点和发展措施
下一篇:略论治水实践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